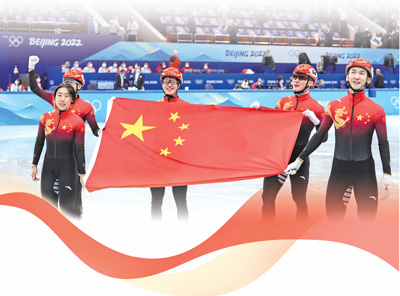【资料图】
【资料图】
我们村是老解放区,那时抗战已经胜利,连喘气都顺当,咱庄里庄乡的,就缺个剧团唱唱戏,耍把耍把、乐呵乐呵了。
说归说,这可不是件容易事。当时,虽说有了土地,能填饱肚皮,不再穿补丁摞补丁的衣服,但兜里没多余的钱。我们村离德州十几里,进一趟城用不了多长时间,但能去德州逛逛的,全村没有几家,更不用说进戏园子看戏了。怎么办?叔叔大爷们有办法,那就是自学、自排、自演。
新中国成立当年,村里就有了剧团。人们习惯叫它“庄户剧团”,说白了就是“庄稼人剧团”。全村上千口人,会吹拉弹唱、能跟着唱片哼两句的人,还真不少。村里凑了点钱,区里又支援了一下,行头、乐器就置办得差不多了。能进小剧团的都有一种荣誉感,没有人提报酬,用今天的话说,都是自觉自愿的“志愿者”。二十多个人的小剧团,什么戏好学好唱,就学什么、演什么,不但能唱河北梆子,也能唱京剧、评剧。演员们初次登场,锣鼓点不齐、演员忘词,是常有的事。唱着唱着忘了词,做“导演”的李爷爷就踩着小碎步从后台上来,凑在演员耳朵上嚓嚓几句,然后颠颠儿地跑回去。每当这个时候,台下就响起一阵善意的笑声,演员一张口,立马静下来,两眼直直地瞅着台上,眨都不眨。
要唱戏,就得有剧场。新中国成立后,德州城建了电影院、剧场,人们仍习惯叫它“戏园子”“电影园子”。戏园子唱戏卖票,观众凭票入座。开戏前先是“打嗵”,也就是敲锣打鼓,是用这种方式告诉人们要开戏了。“打嗵”不是瞎打一气,要像唱歌伴奏一样,按谱子来。一般“打嗵”三遍,才正式开演。这些传统,大都被我们村的小剧团继承下来。但有两处不一样,一是我们村的剧场没有固定地方,哪里宽敞背风,就设在哪里。比方说,剧场本来设在李家大院,年后李家在院子里起了一间房,地方窄了,不适宜当剧场了,就得另找地方。二是不用花钱买票,场内没有座位,要自己带。坐马扎、小板凳的在前,带椅子、板凳的靠后,这是硬规定。在靠前的地方,放上十根八根的檩条,就算是“雅座”了。有时看戏的人多,后面的听不清或看不见,就拼命往里挤,坏小子趁机捣蛋起哄“打哗啦”,弄得人们前仰后合,戏演不下去。出现这种情况,民兵连长就会带民兵到场维持秩序。所以,每当村里唱戏,我总是催着母亲早做饭、早吃饭,找个好地方。如果打了头遍嗵还没吃饭,就干脆不吃了,提着马扎就往剧场那儿跑。因为年龄小,我一个人到场看戏的时候很少,多是与奶奶、母亲一块儿去。看戏的人那叫一个多,老老少少、男男女女,就连平时不大出门的闺女、刚过门的新媳妇,也没了往日的羞怯,早早赶来占地方。人们图的是热闹欢喜,少不了要买些花生瓜子糖果什么的。久而久之,戏场周围就成了小夜市。小贩们多是推着单轮小车,车篷横梁上挂盏提灯,将货物摆在车盘上。还没到戏场,远远的就能闻到一种诱人的味道,馋得人流口水、咽唾沫。不用吆喝,自有大人孩子光顾。我惦记着到场看戏,更惦记着夜市的糖果和香喷喷的包子。
几年下来,小剧团已能唱七八出戏。每年正月初四五就搭台唱戏。为了让人们多看几出戏,就与附近的几个村联合串演。出村串演没有报酬,如果时间晚了,就在村里吃碗面条,吃完这碗面,把嘴一抹,便带上戏箱回去。这样,每个村唱上三五天,就过了正月十五。实际上每村都有几个好角儿。我们村的“梆子腔”最棒,特别是演小生的陈伯,唱得真好。大冬天北风冷得刺骨,人们冻得直打牙巴骨,可中途离场的没有几个人。有一次冻得实在受不了,我硬拉着奶奶、母亲回家,躺在被窝里听。那笛子声、板胡声、陈伯的小生腔,抑扬顿挫,悠扬婉转,灌得村里满满的,陪着我进入梦乡。后来我上初中,读鲁迅先生的 《社戏》,先生童年对社戏的反感,我一点儿也没有。
我们村的庄户剧团自打成立,一直唱到1964年。从此,唱戏改成了演节目,演的当然是歌颂党的政策的,上台的大都是年轻人,但也有例外。一次,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奶奶,踮着一双小脚上台,用半生不熟的京腔说快板儿,风趣又热闹,逗得人们笑弯了腰、乐岔了气。
作者:邓南邨 编辑:李耀荣